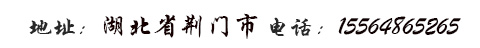群山丨王新军中篇小说少女春麦二
|
作者简介:王新军,国家一级作家,著有《大草滩》《好人王大业》《坏爸爸》《八个家》《最后一个穷人》等小说余万字。曾获上海第六届中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中篇小说奖;连续荣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飞天文艺奖等奖项。被授予“甘肃省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入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现为甘肃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五 王春麦和马石头的这门亲事,在马文革将一条猪腿扛进王大平家之后、在王大平兴高采烈地摆了一桌很不像样的酒席请亲朋们过来酒足饭饱之后、在马文革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掏出裹了两三层破布的那两千块钱之后、在马文革的婆姨为王大平全家老少都挂了一身新衣服、又将王春麦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穿戴一新之后,就正儿八经地确定了下来。 在沙洼洼,这就叫订婚了。 按照双方在订婚仪式上的约定,到死都不能后悔了。 也就是在那个筵席散尽人去屋空的黄昏,王春麦躲到自己的那间小屋里,把曹桂花给她提过来的两套新衣服和两双新皮鞋从包袱里掏出来,放到了她的小床上。她看着那两双样式古怪的黑色女式高跟皮鞋,闻着它们散发出来的刺鼻的人造革和强力胶的混合气味,注视着它们闪烁着的虚假的锃亮,她诚慌诚恐,又心如刀绞。它们多少次穿在别人脚上在她眼前出现过啊,她甚至已经在心里无数次想象过当她那双小巧的脚穿上皮鞋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十多年了,她一直都没有机会去体验。这个梦想终于在她确定了终身大事的这一天实现了。那阵子,王春麦粗粗地喘着气,胸脯一高一低剧烈地起伏着。她的两只手分别握着一只皮鞋,握得紧紧的,好像她一松手它们就会变成两只来路不明的鸟儿,突然从她手里飞走。在沙洼洼,只有婚姻能够实现她想穿一双皮鞋这样一个小之又小的梦想。她紧紧地抿住嘴唇,又用牙齿咬住,她的心里呼噜噜地开始翻涌起潮水来,莫名其妙的波涛在她五脏六腹间汹涌澎湃。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她以后的所有梦想都只能依靠婚姻这唯一的途径来实现?这是什么逻辑呀,理想和婚姻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么?如果真有什么定理或者公式可供套用的话,那是不是说穿上了马家婆姨送来的这双新皮鞋,就得乖乖地在沙洼洼做另外一个马家小婆姨? 她嘴角向上一翘,朝屋角的某个地方轻蔑地扫了一眼,尔后左右开弓,将两只油光锃亮人造革皮鞋扔了出去。 除了婚姻、除了马石头这根稻草,在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荒僻一隅——沙洼洼,她王春麦又能指望什么呢! 六 王春麦接到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封信,是同学罗海燕从州城酒泉写来的。 那时候罗海燕已经去州城一家卫生学校上学快两个月了。就在王春麦认为好朋友罗海燕已经忘了自己而感到绝望的时刻,半月来一次沙洼洼的乡邮员辗转了半天,才把一封印着小燕子图案的信封送到了王春麦的手上。 乡邮员是个风趣的小伙子,他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珠一边打量着王春麦,过了好一会儿才又问了一句:你就是沙洼洼的王春麦?王春麦说,我就是呀。小伙子又问,在沙洼洼,就你一个叫王春麦的?小伙子不知道想问出些啥来,又接着问,这个给你写信来的,是你们家亲戚?王春麦看了看信封上熟悉的略带一点斜的字体,想也不想就说,是我朋友罗海燕写来的,她到酒泉上卫校。小伙子这下放心了,翻开一个夹子指着其中的一格说,那好,你就在这儿签个字吧,这是一封挂号信,你们沙洼洼,已经好几年没人来过挂号信了。 王春麦接过乡邮员递过来的圆珠笔,在指定的方格里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她没有想到王春麦那三个字写得那样难看,“王”字的三横竟然没有写平,“春”字的上面两横给连在了一起,还将下面的“日”字差点错写成“目”字,“麦”字就更没法看了,上半部太大,下面又太小,看上去怪模怪样的。写完了,王春麦突然觉得很脸红。说实在话,自从她会写自己名字的到如今,她觉得从来没有把“王春麦”这三个字写得那样难看过。 乡邮员一时不想走,还想答讪,又要问这又要问那,王春麦支吾一声,一转身就径自进了自家街门。 罗海燕的来信,写了三大页,王春麦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足足读了一后晌。翻来覆去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反正太阳落山的时候,那封信她从头到尾都能一字不漏地默诵下去了。她太想知道城里是个什么样子了,虽然她天天都能从自家那台小小的电视上看到北京呀上海呀这些大城市,但那里毕竟离她、离她们沙洼洼太过遥远。她翻出了地图册,找到了河西走廊中西部那个标着“酒泉”两个字的圆点,然后又在它的东南方向确定了她们沙洼洼的基本位置。没想到这几厘米的距离,一下子就把她和“酒泉”的之间的长度拉近了。罗海燕在信中说,酒泉不但有高楼大厦,还有个古老的钟鼓楼和一个很大的公园。公园里真有一个大湖,湖里还能划船,只是这几年那里面的水有些发臭了。更叫王春麦激动不已的是,那个使一座城市得名的“酒泉”的人,就是她们历史书上学过又在电视剧中看过的汉代征西大将军霍去病。今天的酒泉城,就是当年霍将军大捷之后,将汉武帝御酒倒入泉中与将士们同饮的地方。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那个泉边唐代的好酒的大诗人李白也曾去过,不单单是去了,而且还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诗: 天若不爱酒, 酒仙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泉。 在信中,罗海燕把这些都告诉她了,还抄了这首李白的诗。没想到这些她们课堂听老师说过的东西,离她其实是那样近。当王春麦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几乎连呼吸都要停止了。仿佛罗海燕所说的一切,就在她的眼前。繁华的大街,玲琅满目的精品屋,鳞次栉比的商场店铺,绿树成荫的公园,清凌凌的泉水,雕刻着诗仙李白诗句的汉白玉石碑,这一切的一切,都幻影一样在她脑海里闪现着,就像她的脑袋里安装了一块巨大的彩色屏幕,屏幕上正在播放着有关那座城市的风光片。而她王春麦,则是一个心怀憧憬而身在远方的慕名游客。心向往之,却终因囊中羞涩而不能成行。罗海燕在信的末尾说,如果真的还想上学的话,她完全可以不顾父母的反对和阻挠,只身来酒泉。也不用花别人的钱,完全可以一边打工挣钱,一边上学。 但王春麦仍然觉得,那对她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半个月后,王春麦才给罗海燕回了信。除了诉说一些乡村生活的单调、无聊,告诉她来信收到之外,没有透露有关她今后如何打算的任何信息。 事实上王春麦那时候还没有真正为自己的今后好好打算过。在沙洼洼这么个地方,没有了她爹王大平的支持和允诺,她的前途根本就是一片茫然。王春麦几乎每天都被这个苦恼的现实折磨着。 然而就是那天傍晚,却叫她看到了希望。她把扔到墙角的皮鞋重新拣起来,小心地拭净上面的灰尘,将它们和那两套新衣服一起重新包好了。她想她是不是可以穿着它们,走出沙洼洼,像罗海燕一样,像一个真正的城里姑娘一样,款款地走在城市宽阔平坦的大街上? 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待在沙洼洼的王春麦就因为苦涩的现实更加地苦闷起来。她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她心里的秘密,不管这个人是她的爹妈,还是马石头,或者罗海燕。白天的时候,她像一只离群的孤雁徘徊在村庄周围,她的目光像两把无形的手术刀,她拿着这两把刀子,用她稚嫩的思想,试图解开古老村庄的秘密,试图与沙洼洼达成某种必要的和解。村庄坐落在沙漠边缘的一片洼地上,一户一户人家的土庄子没有规则地散布在前前后后的梁洼里。为了看清村庄的整个面目,她不得不一再地向南边的高处跋涉。 南面的远处,青黛色的祁连山横亘在苍茫的大地上,周围的一切永远也无法逃过它的蔑视。王春麦似乎从来也没有走得离村庄这样远过,她知道,这是她的内心与村庄的距离在发生着变化。越过一道又一道隆起的沙梁土岭,她选了一个最高的地方坐了下来。眼前的情景非常奇怪:眼前那个她生活了十多年的沙洼洼,竟然那样小。几片土黄色的农舍散落在梁坎间一块相对平坦的洼地上,一条分了不少岔子的土路将村庄这儿一片那里一片地分开,又藕断丝连地把它们牵扯在一起。一条大河在不远处暴露出干涸的河床,零星的树木孤苦无依地从低矮的农舍四周抬起头来,像一堆破损的小船上竖着的被风吹旧的桅杆。它们已经没有能力再扬帆远航了,因为船上的水手已经从心底里透出了精神上的老迈。在王春麦迷离的双眼中,耸立在她眼前的应该是高楼,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她脚下也不应该是干渴的沙地和无边的砾石滩,而是无边无际生机盎然的绿色草坪…… 直到这时候,这一辈子究竞怎么过,在王春麦自己心里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打算。根本连一个大概的轮廓也没有。在她人生最初的这十几年里,完全都走在父亲王大平为她设计好的模式中。到了学校,学校和老师又为她设计好了一切,学什么,怎么学,老师已经在她们行进的道路上做好了一块块精致的路标。她人生的每一步,事实上都走在别人的设计中。这种设计,连她先迈哪只脚都事先规定得清清楚楚。 在她离开学校即将成人的时候,她父亲又一次不失时机地为她的后半生标出了一万元的价码。她的无所适从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忐忑不安是显而易见的,她的心有不甘更是像闪烁着的火花一样时刻都在目光中暴露无疑。 她的人生从什么时候开始才能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呢?在王春麦心里,这显然成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她不知道答案,别人也同样不知道答案。 王春麦开始想象罗海燕在酒泉城里上学是一种什么样子?那是一所中专学校,恐怕不会像她们上中学时的那种样子吧?她们是不是每人都有一双新皮鞋,都有一条不怎么长的黑裙子,还有一双长筒丝袜,穿在腿上比最漂亮的皮肤还光滑?她都想象不出罗海燕穿着这样一身,是如何走出教室来到光天化日之下的。那会吸引多少惊羡的目光呢?哦,不会的,城里女孩子一个比一个穿得洋气。也许到了城里,昔日在乡中学里洋气十足的罗海燕就算不得什么了。就像一朵荒山里的野花,开在荒山里自是好看得出奇。把它拿到姹紫嫣红的大型植物园里,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使它不得不张目空叹,充其量,罗海燕只是一朵走进城市这座大花房的荒山野花。然而她毕竟已经走进花房了呵!而她自己,却还在这荒山野地上静静开放,随时都有被风沙摧残的危险。 一朵花到底能不能开放?到底为什么开放? 在哪里开放?为谁而开放? 这都成了困扰在王春麦脑际的无解的多元方程式。 七 时间是最能经得起挥霍的东西。一个冬天就这样被王春麦十分不情愿地放归漫漫时间长河。就像一泓清水,明明知道它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却显得无力把握。在时间面前,王春麦真的成了一个能够手握金卡,挥金如土的家伙。 在她和马石头的婚事明确下来以后,马石头反而不好意思有事没事就往她们家跑了。整个冬天里,她只和他约会过两次,地点都是在南梁后坡那片不大的树林边。他们彼此的身体都被厚重的棉衣包裹着,尽管如此,她还是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马石头在出村的时候就大胆地拉住了她的手,这让她感到温暖。这一次她没有往回抽,她觉得她的手这样被人握着其实挺好的,他们的身体隔着棉衣紧紧挨在一起,也挺好。那时候她竟然能感受到马石头身上那股男人身上特有的烟火气息,这气息叫她产生了一种安全而温暖的感觉。 小树林毕竟不远,即使走得再慢,不一会也还是到了。 那次不欢而散的约会之后,大约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他们又在一个傍晚时分,踩着一层刚没鞋帮子的积雪来到了小树林边。 王春麦就是从那时起讨厌起那片小树林的,她奇怪为什么马石头每次都要把她往这里领。当她把这个问题向他提出来的时候,马石头想了半天,又四下里张望了片刻,然后才沮丧地说,你说,在咱们沙洼洼,除了这处胡杨林子,还有哪里是个适合约会的地方?马石头这一问,居然使王春麦瞠目结舌了。是呵,除了这片尚未枯死的小树林,在这片被风沙侵蚀着的土地上,真找不出第二个如此尚具有一丝浪漫情调的地方。而这个最有浪漫情调的地方,如果不是偶尔一层白雪的点缀,几乎也是可以用荒凉来形容的。而他们的约会,和电视里那些城市青年男女的风花雪月相比,显然是有东施效颦嫌疑的。那样的约会对她和他来说,就像梦一样遥不可及! 她知道他们内心其实是并不缺乏浪漫的。 在这种判断迷失之后,王春麦陷入了苦闷的泥淖当中。她像一只荒原上辨不清方向的羔羊,又如一头山林中迷途的小鹿,她感到一丝莫名的恐惧,它时刻鬼魅一样在她身体四周缠绕。这一下子使得在心中对约会已经稍有渴盼的王春麦,陡然间又变得心灰意冷了。那天晚上,她在离树林还有三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很镇定地站住了。她借着地上白雪折射起来的亮光,紧紧盯住马石头那双被年青的欲火烧烤着的眼睛,任凭他鼻孔里不停地喷出公马一样的鼻息,再也不主动向前走了。 她挺直身子,意味深长地对他说,能在这个小树林约会一次,你就感到非常满足了是不是? 马石头对她的突然发难,并没有及时做出反应。他又上前一步,伸开双臂做了一个搂抱的动作,结果自然是又被王春麦的双手挡了回来。 你先回答我。 王春麦声音冷冷地说。 她的声音在凛冽的空气中显得硬棒棒脆生生的,语速很快,仿佛只是一闪就乒乒乓乓落在了雪地上。王春麦看着马石头的脸,她看到那张脸上的表情渐渐僵住了,僵成了一只吊在风中兀自静默的绿南瓜。 这样相互对视着的无声的缄默,在他们之间持续了很久。他们隔着两三步的距离,倾听着对方错综复杂的呼吸和心跳。 良久,王春麦又说,马石头,你不要像沙洼洼那些没出息的男人那样行不行?就像你爹和我爹,他们一辈子过得有啥出息? 说完王春麦就回头快步向村里走去了,雪在她的脚下发出短促而有力的咯吱声。直到回家进了自己的小屋,她都不清楚二十多分钟前她究竟对马石头说了些什么。在那么一个时段里,她的脑袋一直空空如也。她弄不清她对马石头的感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仿佛这一切与爱或者不爱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对拥抱和接吻这些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年轻人的情感镜头,她也是想试一试的。但每当马石头想在她身上有所举动的时候,都有一股无形的力量促使她最大限度地躲开了他的侵略。在她的潜意识里,像她们沙洼洼这样的地方,是不配有那种动作更不配有那番风情的。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最为经典的婚前男女关系,也只能被人们嗤之为偷鸡摸狗。更可笑的是,早些年在这里人们居然对兄弟两个守着一个媳妇的某些事实能够容忍:邻村后梁上的许大虎和许二虎,兄弟两个三十多了没钱娶媳妇,好容易攒凑了些钱,老大托人有了个媳妇。名誉上这个女人是二虎的嫂子,却跟二虎住在一起的时候居多。奇怪的是没有人对这样的事情说三道四近而干涉不说,竟然还将这个老二美其名曰“帮牛子”。意思是许大虎这只架辕的牛,没有能力把一家的日月拉向一个明亮的光景,但又不想失去女人,于是就找一个没有媳妇的男人,来家里一起搭伙过日子,把一家子的日月过下去。可多少年了过去了,这个“帮牛子”帮来帮去,破家还是一个破家。在老大和村人眼里,倒是的确省下了一笔为兄弟娶婆娘的开销。眼睛一睁一闭间,也就默认了。生下两三个娃,叫叔哩叫爹哩,反正就叫去吧。关于这种婚姻状况,他们说这是老早老早就有的一种暗中默许了的风俗。 愈是在沙洼洼平淡而沉闷的生活里熬煎,王春麦就愈是无休止地向往城市生活。这样的向往促使她建筑在沙洼洼意识上的精神大厦,开始一天天陷落继而坍塌。进入冬天,她躺在母亲为她烧好的热炕上,除了吃饭上茅房,几乎从不出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还时常被自己绵绵不绝的呢喃和梦呓惊醒。学生时代的校园生活梦一样结束了,她像一只破足球,被人遗弃在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她不得不任凭时间白驹过缭般将自己的金色华年一缕缕抹去,在沙洼洼这片土地上,留下被时间描摹出的又一幅苍白的人生画卷。 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王春麦坦然地接受了马石头出门打工之前所作的短暂告别。她为他准备了信纸和信封,她认为他们之间,相隔一段距离之后的交流,空间应当会更宽阔一些。那一次,当马石头递给她二十元钱的时候,她也欣然接受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允许马石头在她身上做出多余的动作。她心里为他们的交往制定的界线是:仅限于拉拉手。至于能不能接吻,在王春麦的脑海里,那差不多都是结婚之后才能做的事情。 八 沙洼洼的春天和以往任何一个春天都没什么不同,播种后的土地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连串长长的等待。那一抹可怜的绿色,牢牢地隐藏在沙土地的深处,迟迟不肯涌现。村庄就像一个临近生产的孕妇,连续不断的阵痛已经折磨得她口干舌燥,憔悴不堪。偶尔风从西边沙漠里生起,卷起连天接地的滚滚黄尘,排山倒海般地压过来,如同一万匹脱缰的野马,将天地之间搅得混沌一片。那时候的沙洼洼,必然是关门闭户的。 大风有时候就刮成了沙尘暴,越往东去,据说越刮得厉害。从电视上看,它竟然还能吹到北京去,迷住北京人的眼睛。大风过后的土地更加焦渴,人们一边忙着清理地里的淤积黄沙,一边重新整理刮出地面的种子。实在不行的,就得重新播种或者改种了。 从马石头离开的那个晚上开始,王春麦就开始盼望能接到他的来信,这是一件很奇怪的心情。同在村里的时候,她不想见他,可以说见了还有点烦。可她一旦知道他出了村,离开沙洼洼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那距离在她脑海里是那样漫长,她心里马上就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她渴望他的来信能给她一个地址,然后她会在地图册上找到那个地方,再把自己在沙洼洼所有不想说的话,一股脑儿告诉他。她连给他回信的信封和信纸都准备好了,就放在她那张小桌的抽屉里,钢笔里也已经吸满了蓝色墨水。每一次拉开抽屉,面对那一沓红格信纸的时候,她都有一种强烈的一吐为快的冲动。说什么,写什么,腹稿她都修改千百遍了。然而,这一天却迟迟不来。她甚至都在想是不是马石头已经把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了?或者又在外面结识了别的女孩子。外面的世界,毕竟不像沙洼洼这样狭小,这样闭塞。从电视上看,外面的世界花花绿绿的什么没有呵。 在王春麦差不多快要绝望的时候,乡邮员那锐利又清脆的摩托车嗽叭声,撕破了笼罩在她心头的阴影。当她从马石头的信中第一次读到“亲爱的春麦”这几个字时,心都快要从张开的嘴巴里跳出来了。骤然而起的剧烈心跳把她的身体从屋子里冲撞出来,一股无形的力量催促她飞快地走出了家门,走过了村街,翻过一道沙梁,越过刚刚涌起一层浅绿的田野。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经停住了脚步将那封信捧在手中按到怦怦乱跳的胸口上的时候时,她才发现自己正站在那片正在吐露新叶的小树林里。 树叶正在艰难地舒展,身边满是白杨树和胡杨树苏醒时散发的带着胶味的清香。那是一个大晌午,没有风,太阳照得大地暖融融的。天蓝得那样深,那样远,天地之间只有寂静的天籁在耳边回响。这一天她盼得那样苦,却来得这样突然,没有一丝先兆,像梦一般。两种情愫的碰撞使王春麦紧张的心情一落千丈。她释然了,一个多月时间里她心率不齐心力憔悴,她的心俨然被一只大手无端地捏紧了。一封马石头的来信,将这一切化为乌有。那一刻,她心里充盈的是幸福,是甜蜜,是慌乱,是快慰的无措。 王春麦找了一块干净一点的地方坐下来,将那几页信纸展开在自己的膝盖上,抑制着自己怦怦的心跳,一字一句地往下读。她不知道她到底读了多少遍,反正到她将它装起来揣进口袋开始回家的时候,一路上她已经能够默诵出这封信的全部内容了。 当天晚上,王春麦就给马石头写好了回信,她几乎没有任何停顿就把那封信一口气写完了。 信发出去以后,她的新一轮绵绵苦盼又重新开始了。有了第一封,对第二封的盼望就更加强烈。她急切地想知道他还要对她说些什么,而对于自己身边的一切,她就显得漠不关心了。她没有想到距离使她和马石头之间发生了如此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就是她心里越来越放不下马石头了,越来越不能没有他了。 在这种复杂而又丰富的情愫中,沙洼洼的春天很快过去了,紧跟着夏天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从王春麦眼前一闪而过。沙洼洼人,经历着和往年一模一样的劳作。等待雨水的来临,等待麦子抽穗继而成熟,然后收割打碾入库,然后在炽热的日子里再次等待秋粮的成熟,盼望它们的丰收。 沙洼洼的日子,在王春麦眼中似乎永远也不会改变,天旱了村民们就由几个老者引领着,去村北那个在原来地基上重新塑起来的龙王庙求雨。求来求去,雨不来,全村人脸上倒是阴云密布了,仿佛举手投足间,就会有碗大的雨点落下来。如果某一天雨终于来了,很多人竟然就把它归功于那一次次全村几乎是集体出动的徒劳无益的上庙祈求。而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印度洋上大面积冷湿空气向西北漂移的结果,这个一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就知道,可笑的是他们却把这个自然的造化说成是龙王爷对受苦人的悲悯和体恤,说成是龙王爷对沙洼洼这片荒原旱地上苦焦民众的眷顾。这一切都叫初中毕业的王春麦感到一丝不由然的愤懑。然而对于这所有的一切,王春麦又是鞭长莫及无能为力的。 一句话,对于像沙洼洼这样一个古老又执拗的村庄,她只是一盘摆不上桌面的小菜——不就一个丫头么! 未完待续…… 原标题:《群山丨王新军中篇小说:少女春麦(二)》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ingdaia.com/qdzz/11578.html
- 上一篇文章: 荆州的别样端午澎湃在线
- 下一篇文章: 绿油油的石砲沟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