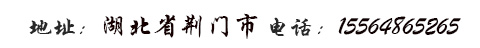夏燕靖唐代ldquo品色衣rdqu
|
年 第02期 夏燕靖 博士,南京艺术学院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艺术史论。 引子我国古代服饰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有着严格的等级、身份和地位的标识,历代官制也都将制定舆服制度作为规范服饰礼仪的重要举措,服饰制度成为封建社会朝廷统治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改正朔,易服色”,这是历朝历代易帜开国的必要之举,以此来确定服饰的规约。由之,章服制度便被列为历代封建王朝舆服制度的重要内容,关涉服色与服饰搭配的各式等级要求,以区别穿着者的身份。在唐代,章服制度就细分为“品色”“章纹”“佩鱼”和“环带”四个部分,而其中的“品色衣”尤具特色,值得深入考察。 “品色衣”制度涉及封建时代官吏所穿常服,即品服,以服色别贵贱、分尊卑,体现的是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服饰形制。如黄色多为古代帝王的专用色。以唐代为例,太宗贞观四年(年)有规定:“官分九品,三品以上着紫色,四品深红,五品浅红,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唐会要》)。这样一来,着紫穿红者便是身居高位者,而青色衣着者官卑职微。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行》),便有遭贬后官职卑微之意。而那些穿红着紫的达官贵人,多半与朝廷关系密切,所谓“红得发紫”就是形容那些仕途顺达、官运亨通的人,即与“品服”有着密切的关系,紫色毕竟是位居皇帝之下的高官服色。“品色衣”制度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北周,至唐代制度逐渐完善。后又经过多次修订,最终在明朝被补服所取代,至清朝终逝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壹唐代的“品色衣”制度《礼记·玉藻》有云:“衣正色,裳间色”,郑注:“谓冕服玄上纁下”,孔疏:“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皇(侃)氏云:‘正谓青、赤、黄、白、黑,五方色也’”。这与“五行”之说相应。战国邹衍提出“五德始终说”,将五行相生相克与朝代更替结合论说。之后,这一观点逐渐普遍,如古史有说周为火德,秦建政后,认为自己是水德,而尚“黑”,以克周“赤”;汉代自封土德,克水,尚“黄”;等等。这些都是古时“正色之尊”的强化观念。至于说“品色衣”规制的出现,现有史料大多指向始于北周,如陈寅恪的考据,已被确证为是有依据的说法。又如关于北周侍卫官的礼服,《周书·宣帝纪》曰:“(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诏天台侍卫之官,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以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有大事,与公服间服之。”当然,考据来看,其制乃完善于隋唐。 如是说来,如何认识“品色衣”制度,除必要的历史脉络梳理外,还要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色彩观念的形成有所了解。依文献稽考来看,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此早有一套解说之理。如《论语》中孔子有言:“君子不以绀鲰饰,红紫不以为亵服”(《乡党》),且“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可见,孔子对服饰色彩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君子服饰不用“绀”(深青带红)或“鲰”(黑色带红)来做镶边,是因红色和紫色为非正色,所以这两种颜色不能用来制作居家穿着的服饰;而异端“紫”色,更不能乱正统“朱”色。孔子是通过色彩来规约服制、明辨是非。由此推断,先秦时期即有以服饰颜色来区别社会身份地位的规制。更何况,以色彩表达至尊观念,这在当时业已成熟。如《周礼·考工记》有曰:“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自古以来,色彩与天、地、衣、裳所涉对象关联紧密,有正色为尊与间色为贱之分。又如《诗经·邺风·绿衣》中卫国夫人庄姜借服色自悼失宠之词:“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按照服饰制度,衣服要以作为正色的黄色为表,作为间色的绿色为里。而庄姜绿衣黄里不符合制度,主次关系颠倒,也就意味着贵贱易序。故而言之,唐代的“品色衣”制度受之影响,其构成对色彩规约定性的观念,不仅蕴含有仪礼文化的互通,而且也是儒学文化中的“礼制”精神的体现。 (一)“品色衣”制度的形成与规约 唐袭隋制。《隋书·礼仪志六》记载:“保定四年,百官始执笏,常服上焉。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大象元年,制冕二十四旒,衣服以二十四章为准。二年下诏,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缋绣为缘,名曰品色衣。”可见,“品色衣”乃指常服,尤其是文献中提及“大象二年”,即北周静帝宇文阐在位第二年(年)下诏:天台近侍及宿卫之官,皆着五色衣,以锦、绮、缋、绣等杂色为缘,名曰品色衣。这说明,史载隋唐时期“品色衣”制度在此时期日趋成熟,乃是沿袭传承了南北朝北周时期的服饰规制而来。之后,便有“自天子逮于胥吏,章服皆有等差”(李上交《近事会元》),“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大滥”(《新唐书·郑余庆传》)。可见,“品色衣”发展至唐代,已渐趋完善,且等级尊卑的观念也日益突出。唐制规定的“紫、绯、绿、青”官服色彩等级制度的背后,是对古制的承袭,并包含有伦理观念、文化精神和佛教传统。 这里,以黄袍作为帝王常服的规制为例,予以详释。《旧唐书·舆服志》:“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这一记载确为当时官服制度的一种呈现,即官服分色从唐开始逐步严格起来。例如,官吏尚有职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哪怕是宰相之职,如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字样;州长官刺吏,亦不拘品级,穿绯袍。又有,在明确帝王着正黄色外,亲王及三品以上着紫,四五品着红,妇人服色从丈夫等规制。由之可见,这种服色制度由来已久,承袭而来的种种观念均呈现出明显的效应。比如,“品色衣”制度所体现的传统伦理文化特性,就显而易见。其基本范围依然是《礼运》所列范畴,而构成的官职与社会关系,经儒学改造和发挥,最终形成的仍然是“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的传统伦理,进而可以高度概括为“君为臣纲”。故“品色衣”规制的背后,突出显现的就是我国古代社会组织万变不离其宗,血亲血缘纽带一直未受到根本的触动,这也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伦理化的秘密之所在,致使服色也被赋予礼仪尊卑伦理文化之内涵。 唐代崇尚黄色与佛教有关。佛教文化与艺术对唐代服色产生了重要影响。佛教庙堂或僧人坐锦以及袈裟长袍往往以色相单一突出为优先选择。事实上,黄色在古印度佛教中是具有最高品质的象征,因为黄色也是大地的颜色,代表稳定和根植的本性,它在佛教中被认为是谦卑和脱离物欲社会的象征,代表着“放弃”。黄色在佛教的地位与象征意义与释迦牟尼的成佛故事有关。释迦牟尼出生于释迦家族,公元前6世纪,在目睹了世间的生老病死之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浮华的一生,宣布放弃皇族身份成为一名托钵者。佛经中描述其所着乞丐袍为各种残破衣服的碎片缝合而成(梵语称为sanskritpāmsūda或pāmsūla),日本研究者将其称为“粪扫衣”。这些碎片被清理后进行缝制,制成一个大到足以环绕和覆盖乞丐的长方形长袍,这就是佛教僧袍的最初形制。然后加以染色,染料由收集到的植物茎、树皮、叶、花或果实(特别是菠萝蜜的树心和树叶)制成。染料的混合制作过程导致了一个混合色的黄土色效果,这种颜色被视为蕴含了放弃世俗文化的价值观、脱离物欲社会的意义。这也是佛传故事中提及的释迦牟尼选择黄色(或者说土色)作为佛袈裟色彩的来源。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地区,黄色依旧被尊为贵色,根据《拔协》记载,赞普敬奉僧人,“哪怕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到一块黄色补丁,也要向之行礼”。 从佛教典籍及《唐六典》记载来看,唐朝廷信奉佛教,出于稳定朝纲之用心,不仅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等级秩序,还竭力采用各种形象化的塑造手段,试图在人们心目中塑造出皇家至高无上、天恩浩荡的形象。故黄色成为至尊之色,既是土地的象征,又代表中央,其寓意乃皇帝主宰四方,这黄色也就成为最高贵的色相,唯有帝王可以穿着。于是,天子开始将黄袍作为专用常服,以至唐高祖武德初年,开始禁止民间使用各种黄色。黄色、黄袍不仅在以后一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占据独尊地位,且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这里,还可以补充一点,即伴随着丝绸之路的传播效应,佛教艺术之花在唐代盛放开来,为唐代服饰色彩的选用增添了靓丽的审美元素。元稹《叙诗寄乐天书》曰:“近世妇人,衣服修广之度及匹配色泽,尤剧怪艳。”“尤剧怪艳”呈现出的正是唐女服饰装扮的基本色调,以此形成了唐代富丽堂皇的服饰风格。 有意思的是,唐高祖武德四年(年)八月,朝廷诏敕三品以上官员“其色紫”,五品以上“其色朱”,六品“其色黄”,流外及庶人“其色通用黄”(《旧唐书·舆服志》)。从这段记载来看,高祖此令应该仅是针对常服而颁布的衣着颜色,并不涉及冕服、朝服与公服,且服色主要是以三品至六品官员的服色为例,还有所谓“六品”能服黄色之说。分析来看,这很有可能是唐朝建立之初,对于服色规制并未严格起来的缘故。有鉴于此,“武德令”于服色之规约显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或许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贞观四年(年)八月,鉴于唐代冕服制度推行完备的条件,太宗又颁布衣服令,继承旧制并逐渐调整完善,提出“寻常服饰,未为差等,今已详定,具如别式,宜即颁下,咸使闻知,于是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下服绯,六品七品以绿,八品九品以青。妇人从夫之色,仍通服黄”。次年八月,太宗又决定进一步完善唐代“品色衣”制度,明确提出:“敕七品以上,服龟甲双巨十花绫,其色绿。九品以上,服丝布及杂小绫。其色青。”(《唐会要》卷三一) 又过了30余年,唐高宗龙朔二年(年)九月,司礼少常伯孙茂道奏称:“准旧令,六品七品著绿,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乱紫,非卑品所服,望请改。六品七品著绿,八品九品著碧,朝参之处,听兼服黄”(《唐会要》卷三一),高宗准奏。十二年之后的上元元年(年)八月,高宗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深绯,十一銙,五品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输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七銙”(《新唐书·舆服志》)。这一规定的内容极其详细,明确了不同品级官吏所穿公服都是有明显等级界限的,具有严格的等级规范。形成这一规约的原因,既有传统的宗法制度所具有的宗法观念,又有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本身等级森严的政治制度的体现。此后,在不到半年时间内,不仅使九品之内官品服色各异,而且还通过服装材质上的花纹、图案、佩戴材料、形状、装饰等,清晰地标示出着装人的身份和等级。从此,正式形成由赤黄、紫、朱、绿、青、黑、白七色构成的“品色衣”制度的颜色序列,成为我国古代社会等级框架的重要标志。这一制度也为后世,主要是宋、明两朝所承袭,成为我国封建王朝“品色衣”制度依据的典范。 综上所述,自隋入唐以来,“品色衣”制度主要是从武德初年开始,在历经了63年的磨合之后,到睿宗文明元年(年)基本定型。这是唐代衣冠服饰承上启下、博采众长的历史的重要节点。“品色衣”规制的普遍推行,使得当时官服的颜色、材质及款式讲究起来。而朝廷对官服制度的每一次变更,又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女性服色。加之“品色衣”与胡服流行相应,中唐之后女服色彩变得更加艳丽夺目,“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唐代王建《宫词》),“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万楚《五日观妓》)。唐代女裙的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奇斗艳,尤以红裙为妍。如武则天《如意娘》诗云:“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石榴裙”以茜草为染料,故又被称为“茜裙”。李群玉《黄陵庙》诗:“黄陵庙前莎草春,黄陵女儿茜裙新。”李中《溪边吟》诗:“茜裙二八采莲去,笑冲微雨上兰舟。”自然,除红裙以外,唐女也穿白裙,名“柳花裙”;又有穿碧绿色裙,名“翠裙”或“翡翠裙”;等等。 自然,唐代“品色衣”制度的形成,除礼仪伦理与佛教文化等因素外,与服饰关系密切的唐织锦,以及服饰染料等相关行业的现实问题,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举例来说,唐代纹锦花色较之前朝更加注重色彩的强烈对比,如日本奈良法隆寺藏唐代联珠狩猎纹锦(图1)就是代表性一例。 ▲图1日本法隆寺藏四天王狩猎纹锦,法隆寺捐出 ▲图2唐变体宝相花纹云头锦鞋,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号墓出土 此外,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唐代云头鞋也具有代表性,此云头鞋尖端夹缀有一条花鸟纹锦(长37cm,宽24.4cm),纹饰为斜纹纬锦,由大红、粉红、白、墨绿、葱绿、黄、宝蓝、墨紫等八色丝线织成(图2)。这两件纹锦花色完全符合唐纹锦的配色规律。若从服饰搭配原则作进一步分析,这样的纹锦和鞋饰花色,一定对服色有着影响,尤其是这纹锦和鞋饰传递出的异域色彩、样貌更值得 再有一点不应被忽略,就是“品色衣”制度的色彩构成,不可能仅仅是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或是艺术的,而应该有其工艺技术成分来作支撑。也就是说,应当从与服饰密切相关的行业来作进一步考察,以获得有力的佐证,这便是唐代服色染料所起到的技术呈色的作用。从《新修本草》和《本草拾遗》等典籍中,我们会发现许多染料并非中原所产,大多是通过与印度的交流而引入的。古印度气候湿热,花草繁多,有着制作天然染料得天独厚的条件。伴随着佛教东传路径的开拓,唐人在承载佛陀图像的唐卡和彩塑上看到印度艳丽的天然植物染料,进而,唐代丝绸上也开始运用植物染料。异邦天然染料的传入,不仅为唐代服色增添了异域色彩,而且也为“品色衣”的色泽选定提供了可能。 (二)“品色衣”的色彩规律 唐代“品色衣”制度,是在经历多次修改更定之后不断完善形成的。归纳来说,经历有五次大的修订,即从武德初年沿袭隋旧制服色,只设三等始,直至贞观四年,高宗对九品服色制定详尽规约,如“紫、深绯、浅绯、深绿、浅绿、深青、浅青、黄铜”。这样的服色规范明示出的等级之规和具体颜色序列见表1所示。 从表1来看,唐代“品色衣”制度中于品级高低和色彩变化之间,遵循着一个基本规律,即尚紫色。这是因为唐代冠服制度在“武德令”推行之后,虽有不断修改完善,但仍上承周制。如此一来,周服尚紫的风气便继承下来,不仅服色,就连服饰搭配、服装质料等方面都依循其制。古时把云霞映成的紫红色气象称为“紫虚”或“紫冥”。唐朝人尚紫尊紫,唐代宋之问《奉和幸韦嗣立山庄侍宴应制》诗曰:“云罕明丹壑,霜笳彻紫虚。”李白《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诗曰:“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从诗词中可看出,紫色作为“贵色”在唐代受到颂扬。 然而,在我国传统礼教观念中,紫色一向被视为是一种“贱色”。作为间色的“紫色”,与“青、赤、黄、白、黑”五种正色相比,代表着卑下和邪恶之相。如《论语》中孔子有“恶紫夺朱”之言,汉刘熙《释名》有曰:“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瑕疵以惑人者也”。的确,紫色在我国古代服饰色彩中是最为敏感的色相。唐制规定大臣们的常服,亲王至三品官人用紫色大科(大团花)绫罗制作,可以看出唐代用色不再是固化的定式。以此分析,唐代着紫色衣也是随着时代风潮转变而发生的。如《旧唐书·舆服志》中有记载,隋初佩绶颜色地位由高至低依次为朱、青、紫、墨、黄。贞观年又规定,三品以上服紫,后因怕“深青乱紫”(深青为古时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得深青泛红之色),故才在上元元年八月下令,文武三品以上服紫。至此,紫色最终超越红色,成为“一色(黄色)之下、万色之上”的名副其实的“贵色”。《旧唐书·舆服志》又记:“开元已来,文官士伍多以紫色皂絁为头巾,平头巾子,相效为雅制。”至此,唐代将紫色尊为贵色,已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有意思的是,《山海经》中记载,有一种神,人首蛇身,常穿紫服。而古代文献中关于紫服被引证最多的当属《资治通鉴》中的记载。相传,道教祖师之一的周朝人尹喜在函谷关任关令,有一天登高望远见天空之上一团雾气自东向西缓缓而来,以为是紫气,示有运将到。此后,老子来到函谷关,他知道尹喜命中注定要得道,于是就在函谷关停留下来,并口述五千言,尹喜将其记录成书,名曰《道德经》。尹喜按照老子教诫修行,果然成仙。尹喜所说的“紫气”,自然就是老子带来的圣人之气。成语“紫气东来”就代表吉祥、祥瑞和福佑。紫色用于服色,代表尊贵之意与此相关。 紫色成为“品色衣”制度中三品以上官员的服色,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道教观念的影响。关于尚紫与道教炼金术之间的重要关联还有两个依据。 首先,唐代奉道教为国教,唐太宗就曾颁《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令,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即老子)”;乾封元年(年),唐高宗尊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而道教以紫色为至尊,将神仙居住之地称为“紫府”“紫台”“紫海”,玉液则称为“紫河车”。这多少在“品色衣”制度初期阶段产生影响,而被制定为上等服色,并在多次改动中从未发生变化。 其次,近年来国外考古化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成果,即对中国“汉蓝”与“汉紫”的研究亦可用来解释唐代尚紫与道教的关系。美国弗利尔研究所伊丽莎白·菲兹胡(FitzHugh)女士从战国至汉代陶器、青铜器彩绘颜料及蓝紫色八棱柱中分析出蓝色和紫色硅酸铜钡,并将它们命名为“汉蓝”与“汉紫”。20世纪90年代,我国秦俑博物馆与德国巴伐利亚州文物保护局合作,在秦俑颜料中分析出了一种目前还未在自然界发现的紫色颜料——硅酸铜钡。直到19世纪,世界上大多数颜料都是以自然存在的有色矿物和染料为基础的,有三个显著的例外:埃及蓝,玛雅蓝和中国蓝、紫色。前两种是碱土金属铜硅酸盐,由于这种成分上的相似性,有人提出中国颜料来源于埃及蓝。受到斯坦福跨学科研究所资助的刘博士团队对秦始皇兵马俑所着紫色色素进行了分析,发现尽管与埃及蓝的结构相似,但中国紫色的微观结构形态却非常不同。通过化学分析,他们认为“汉紫”的合成技术是高折射率玻璃的副产品(即人造玉石)。紫色不仅在秦皇帝的兵马俑的外衣上用作颜料,还广泛用于珠子和耳环,以及汉代墓葬壁画。“汉蓝”与“汉紫”的出土量与中国古代道教兴盛与衰落的历史契合度极高,“汉蓝”与“汉紫”极有可能是当时道士在实施炼金术的过程中合成的。 综上所述,紫色受推崇及其颜料的提炼都与道教关联密切。南北朝时期是道教盛行同时也是紫色的上升时期,隋唐时期,统治者笃信道教并且利用和扶持道教使得这一时期道教推崇的紫色上升到三品以上官员的服色。此外,从印染工艺角度来看,紫色是由红色与蓝色合成的颜色,但它既不像红色那么鲜亮,也不像蓝色那么冰冷,且浸染方法及成本颇高。这也是紫色作为尊贵之色的重要原因。 进而言之,“品色衣”制度中的“紫”与“绿”这两种所谓的“间色”,代替正色登上大雅之堂,这一转变亦是对正色至尊观念的冲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经历了南北朝这一段所谓“五胡乱华”的特殊时期,受到少数民族的审美与宗教因素的影响,中原汉族对色彩的定义与分级也经历了重建。唐王朝自上而下对传统的束缚有着一定冲击力。当然,这种冲击其实也是文化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自魏晋以来,社会上就兴起了一股反传统的风气,经过南北朝的强化,到隋唐已成为自然的状况。唐代能冲破樊笼,形成新制也是不足为奇的,唐人喜穿胡服、女着男装皆为例证。品色衣制度的完善说明传统的正色至尊观念的衰落。加上浅绯、浅青的应用,说明唐代已具备审美意义上的色彩选择力,并形成了新的色彩观。 那么,再说绯色。“‘绯’帛赤色也”,“佩服上色紫与绯”(韩愈《区弘南归》)。这一色彩即深红色,一直为古人所偏爱。如有称“绯桃”(红色桃花)、“绯衣”(古代朝官的红色品服)、“绯衫”和“绯袍”等。笼统地说,红色与黄色是古代色彩中的“至尊”色,红色是热情奔放美好的,在“品色衣”中等级仅次于紫色,成为四品和五品官员服色。暖色尊于冷色,如绿、青、碧三种颜色品级较低,不只是在官服和礼服中,常服中青色也是较为低下的颜色,地位低下的婢女便有“青衣”之称。青衣为下层人士所着,受下层人士喜爱,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染青之蓝草易得。蓝草是一种南北皆宜种易取的植物染料,自周代设染人以后,便有专人采蓝染色,如《毛诗·小雅·采绿》中“终朝采绿。不盈一掬。予发曲局。薄言归沐。终朝采蓝。不盈一襜。五日为期。六日不詹”。楚国设有工官“蓝尹”,专门主持靛蓝生产。至汉代,蓝草更是成为专门性的经济作物,由农户种植以供染色。赵岐《蓝赋》序:“余就医偃师,道往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绀为业,蓝田弥望,黍稷不值。”也正是因为染色原料的普及,青色逐渐平民化。另外,“五色”观念在古代社会根深蒂固,如朝廷只允许民众服黑、白、青三色,而黑、白色又常用于祭祀、丧礼。于是,青色自然而然便成为人们的唯一选择,谈不上喜爱,而成为“流行”。而青衣作为下层人士能够穿的正色服装,久而久之又成为平民及婢女的代称。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品色衣”中的同类色中,深色尊于浅色。上元元年之后,为了将官员品级区分得更加细致,采用了深色尊于浅色的方法,如深绯高于浅绯,深绿高于浅绿等,反映出同等色相中深色尊于浅色的现象,如表1所示。 总之,“品色衣”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服色制度中最具代表性的制度,而唐代是“品色衣”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这与唐代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相关。唐代的多民族文化交融对服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藩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另外,唐代绘画作品和墓室壁画中都有外来使臣拜见的场景,如阎立本的绘画作品《步辇图》(图3)、章怀太子墓壁画(图4)。可以看出,多民族文化交流、文化渗透对服装色彩款式多有影响,从中原宽袖大衫到小袖长裤长靴,中原传统正色到多种间色使用,都与民族交流关系较大。唐代社会生活突出特点为胡化现象,且此胡化现象涵盖百姓生活方方面面。这种民族服饰文化融合致使唐代服色产生了浓艳、绚丽、张扬的色彩,成为服饰史上的典范。“品色衣”制度规范了官吏服装的同时,也对女性服色有较大的影响。“妇从夫色”的规定是男权社会的体现,女子服装颜色应该与其夫品级相匹配,女性服色虽不如品服规定严格,但也受其影响。加上唐代特有的多民族交融文化背景,女性服装色彩吸收了异域风情,更加绚烂。 ▲图3(唐)阎立本《步辇图》 ▲图4唐章怀太子墓壁画 贰唐代女性服装色彩就服色而论,唐代服色乃是我国中古时期最为大胆、绚丽、浓艳亦是最为张扬的典范。唐代服色制度明确规定,文武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均需按官阶穿着相应的色系服饰,对于女性又有追加规制,即依照其夫或子的品级选择相应服色。这是唐代服色制度对女性身份、地位进行的等级衡量。但其间在特定场合,尤其是女性生活的圈子里,服色有了大胆突破。 《新唐书·五行志》记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很显然,太平公主的女扮男装有悖于《礼记·内则》明文规定“男女不通衣服”的教条,但高宗对公主的态度不仅宽容且有几分欣赏,这说明唐代的服饰规约已经有了突破性的变革。不止于此,唐代女装在“袒露”禁忌方面也有突破。例如,在永泰公主墓东墙壁画上绘有一位典型的唐代女性形象,她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着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这华美、性感而富有风情的形象在文人骚客笔下多有赞叹。唐诗人李群玉诗云:“胸前瑞雪灯斜照,眼底桃花酒半醺。”(《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方干《赠美人》诗句更是直面描写:“直缘多艺用心劳,心路玲珑格调高。舞袖低徊真蛱蝶,朱唇深浅假樱桃。粉胸半掩疑晴雪,醉眼斜回小样刀。” 其实,从出土唐俑以及壁画资料来看,初唐时期妇女服饰较为保守不袒露,盛唐开始盛行花样服色加上开放袒领,早先也只是在后宫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唐墓门石刻画及大量陶制女俑均有所见,说明袒领潮流已经遍及黎庶。故周昉《簪花仕女图》中的女服花样就绝不是一种大胆的艺术想象,足以表明当年唐女衣着的开放程度。如此仅从唐代不同时期女性服色作比较考察,就证明其女性服色经历了一个由继承到突破,以至融合域外各等服色的发展过程,这是唐代女性服色走向多元化的真实显现。故透过唐代女性服色的变化,可以了解唐代社会审美风尚与社会心理的不断转变。 (一)唐代女性礼服服色 唐“武德令”规定:“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然而,相对于男性服色而言,对女性服色的管制较为宽松。《旧唐书·舆服志》曰:“既不在公庭,而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对照文献记载来分析,构成唐女服色的花样之姿,应是中晚唐并传至五代。 比如袆衣,这是《周礼》所记命妇六服之一,为后妃祭服,属朝服“三翟”中最隆重的一种。《周礼·天官·内司服》曰:“掌王后之六服:袆衣、褕狄、阙狄、鞠衣、襢衣、褖衣。”因《周礼》的典范作用,袆衣便成为后世皇后的最高形制的礼服,即祭服,也是朝服和册封、婚礼时穿着的吉服。《旧唐书·舆服志》记载:“袆衣,首饰花十二树,并两博鬓,其衣以深青织成为之,文为翚翟之形。素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罗縠褾、襈,褾、襈皆用朱色也。蔽膝,随裳色,以緅为领,用翟为章,三等。大带,随衣色,朱里,纰其外,上以朱锦,下以绿锦,纽约用青组。以青衣,革带,青袜、舄,舄加金饰。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绶。章彩尺寸与乘舆同。受册、助祭、朝会诸大事则服之。”后世袆衣沿袭唐制。然而,没有传世的唐代皇后画像可供参考,如今只能从宋、明的皇后画像中探寻其原型。 而与祎衣及褕翟、鞠衣、钿钗礼衣、花钗礼衣、大袖连裳相配套穿着的素纱中单,则是唐代女服中的一个特例。这是以轻薄的纱罗裁制而成的单衣或夹衣,其花色多样,色泽并无特别限制。长度一般都在两米以上,穿着时将其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于两臂之间,行走起来,随着手臂的摆动而不时飘舞。这种仅以轻纱蔽体的装束,可谓是唐女服的一大创举。 表2所列为唐代女性礼服的基本形制,相比于男子官服要简单得多。其服色也与男礼服的“玄衣裳”大为不同,主要用青色,以深青较青色更为隆重。从“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古语中可以看出,青色染料是从菘蓝和蓼蓝植物中提炼出来的,但其颜色比原植物更深。青色则是蓝与绿之间的过渡色。《旧唐书·高宗纪》“上元元年八月戊戌”条,略云:“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绯,五品浅绯,六品深绿,七品浅绿,八品深青,九品浅青。”显然,“八品深青”色偏于青黑色,较浅青色更高一品。明末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彰施第三》中对草木染色工艺法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可作为染青色的参考。其曰:“染包头青色。此黑不出蓝靛,用栗壳或莲子壳煎煮一日,漉起,然后入铁砂、皂矾锅内,再煮一宵即成深黑色。染毛青布色法。布青初尚芜湖千百年矣。以其浆碾成青光,边方外国皆贵重之。人情久则生厌。毛青乃出近代,其法取松江美布染成深青,不复浆碾,吹干,用胶水参豆浆水一过。先蓄好靛,名曰标缸。入内薄染即起,红焰之色隐然,此布一时重用。”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语出《荀子·劝学》。这里的“青”,实际上指的是一种介于蓝和紫之间的颜色,有如“群青”“青莲”二色。非专业说法,通常会归为紫色,可实际上它是单独一个色系,即青色系。在我国南方方言中,乃有明确的“青色”概念。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载:“二三月间,田苗已长,商家以钱给农户,俟熟收粮,谓之买青。”这里的“青”特指没有成熟的庄稼。此外,青色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庄重古朴、坚强、希望,因此传统服饰与器物常用青色代表此种寓意。 隋唐礼服中,有一特别之处在于男女穿“套衫”式或领口宽大的“背子”对襟服。“背子”样式的对襟服穿着方便,深受女性喜爱,在各个阶层流行。但是平常女子所穿“背子”与后宫嫔妃、豪门贵妇差别甚远,在面料、做工、装饰上逊色很多,且服色一般为白色,在领子、袖口和下摆处只有深色的厚质面料作装饰。唐女礼服中还有一种与之相似的服饰,但更“时尚”,即穿在衣衫外面作为装点配饰,在唐女舞佣中常能见到的,叫做“缦衫”。“背子”与“缦衫”在唐代的盛行与当时乐舞的繁盛有密切关系,一是因为便于换装,二是有装饰作用。 唐代注重歌舞声容与服饰效果的综合展现,这也是唐代女性服饰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唐代舞蹈种类之多可见《唐六典》和《文献通考》等文献记载,不同舞蹈定制不同舞服。如“九功舞”戴“进德冠”(形制介于“进贤冠”与“通天冠”之间的一种非常华贵的冠式),着“紫裤襦”;又如“上元舞”着画云五色衣;“大定舞”披五彩纹甲,持槊;“霓裳舞”则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珮珊珊……唐代舞服细节设计很是讲究,色彩绚丽多姿。如唐宫廷乐舞“圣寿乐”的服饰,衣襟上都刺绣有大团花,在绣衣上再外罩一件与绣衣颜色基本相仿的短缦衫,展现出舞蹈演员的风姿卓韵。“缦衫”是唐代特有的舞蹈服饰,短小,穿脱极为方便。唐人崔令钦《教坊记》记载:“圣寿乐,舞女襟(衣襟)一大窠(布囊),皆随其衣本色。制纯缦衫,下才及带(腰带)。若汗衫者以笼之,所以藏绣窠也。舞人初出舞次,皆是缦衣。舞至第三叠,相聚场中,即于众中从领上抽去笼衫,各内怀中。观众忽见众女咸文绣炳焕,莫不惊异。”唐代舞女正是利用缦衫短小、易于穿脱的特点,在外衣的衣襟处,缝制一个口袋,用于装入缦衫。舞者出现时,观众看见她们穿的只是一种单色的舞服,而当舞到第二叠时,舞者相聚到场中,当即从领上抽去笼衫,放入衣襟口袋。当舞女们迅速脱去缦衫,顿时变换成彩绣裙装,光彩照人,使观众忽见众女“文绣炳焕,莫不惊异”。这种舞服与舞蹈进程相配设计,时空交错,使观众获得色彩变幻的新奇感受。 (二)唐代女性常服服色 将常服纳入服色制度,应该是隋炀帝的一大创举。从大业六年(年)开始,隋炀帝便下诏确定官员服色规制。与此同时,又将服色制度扩大至常服领域,这在《隋书·礼仪志》中有所记载。 入唐以后,在隋制基础上又有调整,以散官品级为基准,分别定出相应的服色,这构成了唐常服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例如,有文献记载:“唐时臣僚章服不论职事官之崇卑,唯论散官之品秩。虽宰相之尊,而散官未及三品,犹以赐紫系衔。……而散官未到金紫银青,则非赐不得衣紫。唐人之重散官如此。”对常服提出的要求,僭越违制自然不可。但这是一个难以控制又难以彻底解决的问题,诸如,在太宗贞观四年(年)、高宗上元元年(年)、宣宗大中六年(年)均颁布有诏令,但服色违制现象一直未能断绝。基于这样的现实,唐代对于女子常服的规约,也同样难以严格执行,朝廷虽多次下令禁止不合规定者,可往往收效甚微。所以,唐代女子常服的变化倒是最能反映当时社会变迁的基本状况,也成为当今研究唐代服色制度的另样素材。尤其是就服饰穿着规律而言,往往女性比男性更容易从服色中显露出自己的心理倾向。故而,通过对唐代女性常服服色的考察,可以探究唐代“品色衣”制度的某些真实情形。 比如,从史料记载和墓室画像分析来看,唐代女性常服最有代表性的是襦裙装、女着男装这两类服饰。其中襦裙最为绚烂,它主要是上着短襦或衫,下着长裙,肩搭帔帛,加半臂,足蹬凤头丝履或精编草履。无论是唐代文学作品,还是各种绘画、雕塑(唐俑)等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对襦裙装情有独钟,有许多描绘。 从表3中可见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唐代女性常服喜用红色。其实,何止是女性常服,隋唐时期民间多喜欢红色。红色意味着喜气,也代表着热情,是一种富有赞美诗意味的色彩,偏好红色正是唐代认知色彩比较普遍的一种心理定式。在《全唐诗》中,“红裙”一词多次出现,这应该是诗人对红裙倍加珍视的感情流露。例如,元稹《晚宴湘亭》诗曰:“舞旋红裙急,歌垂碧袖长。”又如,杜甫《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之二诗云:“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再如,万楚《五日观妓》诗吟:“眉黛夺将首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 事实上,《全唐诗》中,除“红裙”外,红色系列词与“衣”“衫”“袍”“服”等的组合还有许多。像“朱衣”,在王建《宫词一百首》中有诗云:“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裤朱衣四队行。”“傩”是古时风俗,乃迎神驱疫的表演活动。“画裤”为施以彩绘的裤子,多为乐工、歌舞伎穿着。对于特殊职业者,这样的“朱衣”和“画裤”可算是常服了。又如,王丽真《字字双》曰:“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诗中的“朱衣”,应指女服中的大红色上衣。还有“朱衫”“绯衣”“绯衫”“茜衣”“茜衫”“茜服”“绛衣”“丹服”“赤衣”等等,都与红色有关。有意思的是,从唐代“品色衣”规制来看,红色乃服色中的“贵色”,其等级仅次于黄色和紫色,四品和五品官员的服色。然而,这样的规制似乎在日常生活里并未获得严格执行。比如,“红袍”和“红衫”,前者是帝王服色或为将军所穿服色,然而女子常服的“红衫”,竟然也是市井常见的普通服色。如是说来,红色几无等级之别。 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无论是从唐代传世画作还是考古资料来看,其他色彩与红色搭配都是以突出红色为主要目的。还有一类为红色与素色搭配,如阎立本《步辇图》所绘宫女的上身衣着均为白衫,下穿曳地长裙,在腰的左侧垂有一条绶带,带上打有一结,长裙为红白相间色。这是从初唐一直到盛唐流行的裙装搭配,另外还流行有红、绿、紫、黄等几种色彩的搭配。再有,红绿搭配也较为有特色,如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图5)中的几位夫人所穿服饰,为浅绿配粉红,设色可谓浓淡适中。如若细看,几位夫人又可说是“素面朝天”,似张祜的《集灵台》讽喻诗曰“淡扫蛾眉朝至尊”。虢国夫人是否常态如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唐代女性确有淡妆流行,甚至只是在面庞或额上略施黄粉,乃“啼妆”者,这样的流行妆容,或许只能相配如此衣装。再如,周昉《簪花仕女图》《虢练图》和《挥扇仕女图》等,从所绘女性服色来看,大多是绿衫配白裙、白衫配绿裙或是白衫配红裙,也有红蓝裙或类似青衫配套,设色素淡。《簪花仕女图》(图6)中的女性,身上有三四块红色,衬在白色透明的纱幔帔帛里。而且,红裙上虽有绿蓝紫色的纹饰,但红色未受到抑制,仍呈现为一种最强烈的色相,依然跳跃。唐诗曰“宫花寂寞红”(元稹《行宫》),这表明红色乃女性身着华丽彩服,即绫罗绸缎的正色。这也证明,唐女常服又有多样的配色关系,与“品色衣”规制之间虽有关联,但并非受其严格约束。 ▲图5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 ▲图6周昉《簪花仕女图》 再有一点,唐代女常服中有一种“青衫”,是女着男装的一种穿着款式。“青衫”大概是从唐代官吏袍服引申而来的一种说法。然而,《旧唐书·哀帝纪》有曰:“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这“蓝衫”可能是通称八、九品小官吏的服色。可见,“蓝衫”级别很低,几乎与普通百姓衣着相同,故“蓝衫”又可指称穷苦人服装。本文这里所说的唐女常服“青衫”,可能是一种款色,而不太可能是“蓝衫”,且史料记载的女着男装则为胡服,似乎与“蓝衫”无关联,特此说明。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性的显现。《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新唐书·舆服志》又有:“中宗后……宫人从驾,皆胡冒(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唐代女着男装的主色调也经历了变化过程,由初唐时的黑白两色,到盛唐时面料花纹的繁复华丽,再到中晚唐时期服色趋于敛和,面料纹饰增加等,特别是对青蓝之色的使用渐渐普及。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唐代官服中,如“褕翟”为王后从王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祭服,乃青色衣,画褕翟纹十二章纹,褕翟羽色亦为五彩。还有“禄衣”为王后燕居时的常服,亦为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由此可见,常服与官服有界线,也没有界线,这在表3中多少有所体现。 表3选择以“襦裙装”为例,主要是因为此装束乃唐代女子常服中最具代表性的服饰。“襦裙装”是胡服与中原服饰结合的产物,上衣为襦是各个阶层的常服,一般很短,只到腰,佩帔帛,加半臂(即短袖),下着长裙。唐诗中有许多对女性服色的描写,也是“襦裙装”。如白居易《卢侍御四妓乞诗》云:“眉黛夺得置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这是红色襦裙装;卢照邻《长安古意》云:“娼家日暮紫罗裙”,这是紫色襦裙装;王涯《宫词三十首》之二十六曰:“绕树宫娥著绛裙”,这是绛红色襦裙装;和凝《何满子》曰:“却爱蓝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这是蓝青色襦裙装;等等。唐代襦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 (三)唐代女性妆容色彩 “品色衣”制度看似针对服色,其实牵涉面甚广。妆容是整体服饰装扮的一部分,其与服饰间有着相互牵连的密切关系。而从妆容特点来看,唐代“品色衣”制度的影响也绝非仅限于服色,而是涉及服色与妆容的整体效果。况且,盛唐女性崇尚浓妆,可说是我国古代女性妆容史上最为富丽,也最为雍容华贵的形象塑造。如此,怎能忽视妆容色彩与“品色衣”制度构成的关系呢? 相传唐玄宗有眉癖,曾令画工作《十眉图》,而成为宫女描眉之模本。自然,这也表现出唐女对于眉妆的不懈追求,不但体现在眉色的多样性上,还体现在眉形的层出不穷上。当时眉妆的色彩抑或眉形的塑造,很可能是要与服色形成和谐的统一性。只可惜这《十眉图》早已失传,徒留风雅的眉名供后人想象。然而,清代徐士俊据此作有《十眉谣》,多少为我们弥补了一些遗憾。至于徐氏还原程度如何,并不重要。我们相信起码在清代,女性妆容的基本现实与条件,较之如今要靠近中古时代许多。徐氏对十种眉形逐一咏叹,分别为:鸳鸯、小山、五岳、三峰、垂珠、却月、分梢、涵烟、拂云、倒晕。例如,关于小山眉,描写道:“春山虽小,能起云头。双眉如许,能载闲愁。山若欲雨,眉亦应语”;关于涵烟眉,形容道:“汝作烟涵,侬作烟视。回身见郎旋下帘,郎欲抱,侬若烟然”;关于拂云眉,描述道:“梦游高唐观,云气正当眉,晓风吹不断”。《十眉谣》可谓字字珠玑,想象旖旎,是否如唐女真容已无关紧要。 当然,从史实考证来说,相传或仿说毕竟不可作为事实依据,那么,出土文物或更为有力的证据。唐李宪为睿宗皇帝嫡长子所建墓(以下简称“李宪墓”)中出土的大量壁画及庑殿式石椁线刻仕女组图,甬道东、西壁及石椁线刻上的仕女多为出茧眉,而墓室壁画中的仕女多是桂叶眉。此外,还有蛾眉、柳眉、却月眉等。所以,眉式装扮,有“画眉”“描眉”之称,这样的眉形多以青黑色,即“黛”为之。唐代女性以黛眉、朱唇为尚,妆容极具层次感。如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中有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这其中描述的青黛眉,就是“黛眉”之一种。而唐朝的女性,画眉形式又岂止这十种,还流行有各种“蛾眉”,隋唐其他墓室壁画或石刻出土文物,以及相关物像资料均可以证实。比如,唐代长蛾眉流行,但比之前朝已阔了许多,甚而画作柳叶状,“芙蓉如面柳如眉”,形成柳眉梅额新倩妆。这在贞观年间阎立本《步辇图》、天宝年间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以及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均有比较清晰的描绘。可以说,从眉形的变化中可以推测出些许流行时尚。唐诗中亦多有提及,如李白《浣纱石上女》诗吟:“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这“青蛾”分明是指浓黑蛾眉,唐新城长公主墓室的仕女图壁画也多绘有此眉形。 丰腴婀娜的身姿、华美飘逸的衣着,尤其是刻画生动的面妆,都生动地再现了大唐盛世的女性形象。恰如唐诗云:“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杜甫《丽人行》)这些同样在“李宪墓”第二天井东、西壁画仕女图的六个女吏形象上有所展现。值得注意的是,这六位女性的面妆基本符合文献记载的唐女妆容,除额头、鼻梁、下颌露出白粉底妆外,余处皆涂红彩,可谓浓艳如戏妆,与初唐女妆的淡雅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近年来在西安南郊陆续出土的唐代墓葬(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年发掘为例)中,也有类似面妆如霞的侍女陶俑,其年代大约是在肃宗前后。白居易《时世妆》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似含悲啼。”从中亦可看出,唐元和之前,确曾流行过赭面妆。李宪墓壁画中所绘仕女涂浓艳面妆,还有桃花妆、酒晕妆等。而“时世妆”于玄宗天宝年间兴起,至宪宗元和之前方止。其初起于宫廷,“李宪墓”壁画可为实例,从妆扮者年龄推断来看,多为年轻女子。 唐女子面妆主要是对眉与唇的修饰。诗曰:“有个娇娆如玉,夜夜绣屏孤宿,闲抱琵琶寻旧曲,远山眉黛绿。”(五代韦庄《谒金门·春漏促》)又有云“朱唇未动,先觉口脂香。”(五代韦庄《江城子》)李白亦有诗曰:“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浣纱石上女》)诗中所谓“青蛾”应是指青黛眉,但自从杨玉环得宠后,黑色眉就取代青黛眉成为唐女一时间的流行时尚。徐凝《宫中曲》:“一旦新妆批旧样,六宫争画黑烟眉。”依照《新唐书》记载的杨贵妃真容,其形象为高耸发鬓,头发乌黑,鬓发处插有金色小钗数枚;柳叶眉,桃花妆,恰如“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李白《清平调》)。而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在此眉色基础上更为我们道出了杨氏的眉形特点,乃“芙蓉如面柳如眉。”在唐代,柳叶眉虽然没有像桂叶眉那样夸张,但给人印象深刻,“俊眉修眼,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成为后世的一种共识。这种眉形一直流行到了晚唐,吴融《还俗尼》中写道:“柳眉梅额倩妆新”。韦庄另有《女冠子》:“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同时,文献有记载,仅晚唐,唇式就出现了十七种之多,当时的唇妆种类也异常丰富,有圆形、心形、鞍形等。樱桃形和花朵形是唐代最为风靡的两种唇妆,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樱桃小口”乃是源自白居易家蓄养的家伎樊素。眉色和唇妆可谓面容的主要妆容,其色泽定调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形象塑造。可以试想,唐女衣着色彩关乎“品色衣”制度的种种选择,那么,妆容特点在其中定是重要的参照指标,服饰装扮乃是整体,缺一不可。只是从现有文献史料还难以直接获得证据,在此仅作推理考察。 除此而外,笑靥妆扮也尤为突出,这是造成顾盼生姿效果的点睛之笔。如此这般,便无须再去寻求什么别样花色了。说到面靥,段成式《酉阳杂俎·黥》中有一小典故:“近代妆尚靥如射月,曰黄星靥,靥钿之名,盖自吴孙和邓夫人也。和宠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婉弥苦。命太医合药,医言得白獭髓杂玉与虎珀屑,当灭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虎珀太多,及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意,视之,更益甚妍也。诸婢欲要宠者,皆以丹青点颊而进幸焉。今妇人面饰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赐,以掩点迹。大历已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辄印面,故有月点钱点。” 有关面靥,从敦煌石窟壁画描绘的一批“供养人”形象中可以获得佐证。这类壁画所绘面靥,突出的是女性脸颊妆彩的“点子”,面颊两侧对称,仔细品味,确实点出了风韵,极具美容效果。所谓“供养人”,即是石窟出资赞助人。画面上的人像,尤其是女供养人像,自然是要端庄美丽,面颊妆点也就是段成式所记述的女性“妆尚靥”,又叫“黄星靥”。这“星”即“点”的意思,点妆位置就在脸上特有的“靥”处,以点志靥,为求得妩媚之容。段成式说“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赐”,这正好与敦煌唐代壁画面颊“星靥”相吻合。段成式说“靥钿”起因颇具偶然性,不小心弄破了脸皮或遭破相而造成的伤痕,渐渐变成了自觉地进行脸颊点饰。本为遮丑,反其道而行之,却得到了面容妆扮的情趣。“青点”“红点”点脸竟成了女性邀宠一艺。 唐女喜脸上敷粉,又在颊边画俩新月或钱样,名“妆靥”。有的更是在嘴角酒窝间加两小点胭脂,或用金箔剪刻成花纹贴在额上或两眉间。这种贴金箔花纹,就叫“金钿”;若用在两颊的,称为“靥钿”。妆靥的具体形状花色各异,盛唐之前,一般作黄豆般的两个圆点。盛唐之后,面靥的范围有所扩大,式样也更加丰富,这才有形如钱币的“钱靥”,或是状如杏桃的“杏靥”。讲究的还在面靥的周围饰以各种花卉,俗称“花靥”。唐女面饰除了“靥钿”,还有额黄、斜红、花钿,独特的妆饰与广为流行的浓艳“红妆”相配,观赏性极佳。点靥妆扮虽说比不上眉色唇妆那么显著,但不得不承认,其依然有着点睛之妙,在女性的整个装扮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也必然会对唐女在“品色衣”制度下的着装选择,或曰装扮搭配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唐代女性偏爱明艳靓丽的色彩,配色大胆,虽多受“品色衣”制度的规约,但毕竟常服很难管控。也就是说,除了宫廷服饰有基本规定之外,日常服色与妆扮还是可以随自己的心愿喜好来选择搭配。然而,由于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交融的影响,唐代女性服饰和妆容色彩也呈现阶段性的特色,由温和秀美到浓艳华丽再到雅致清丽,展现出唐代各时段的不同风格,共同构成“品色衣”制度下的妖娆之姿。 结语唐代色彩观,总体来说就是传统色彩观的继承和再现,即“五色观”作为这一观念的审美基准,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色彩观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色彩观融合的结果,以“青、赤、黄、白、黑”的色相来传达情感和意志。诸如,《周礼·考工记》记载:“画繢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西方谓之白,南方谓之赤,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这是将五色崇拜和五行色彩同方位进行的联系,由此推论出万物之色缘于五色调和。《礼记·檀弓》记载:“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这是对五色观立意更完整的阐释。根据这一认识的推理,舜以土德王,尚黄色;夏以木德王,尚青色;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周以下以水德王,尚黑色;西汉为克水而以土德王,尚黄色;东汉为抬高君权,突出了“五行”和“五方”中的“土层中央”的观点,将土视为一切的根本,从而突出了黄色的地位。又《礼记·玉藻》记载:“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纯组绶,士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玟而缊组绶。”《春秋谷梁传》记载:“礼楹,天子丹(朱红色),诸侯黝垩(黑白色),大夫苍(青色),士黄之。”这表明从《礼记》到《春秋谷梁传》已确认出色彩的尊卑等级。 这样的传统色彩观,在西周至春秋时已影响到服饰色彩的尊卑等级。如周代礼乐制度确立以后,色彩便主要用以区分等级差异,其使用范围主要是车马服饰。服色以赤、玄二色为尊。《诗经·曹风·候人》有曰:“彼其之子,三白赤芾。”毛传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轩。”《论语·乡党》曰:“红、紫不以为亵服。”古时红色为“朱”,很是贵重,“红”和“紫”同属此类。除赤色以外,玄色也被周人视为贵色、吉色,贵族常用黑色衣料来制作礼服,于祭祀、婚仪、冠礼等庄重场合穿着。《荀子·富国篇》曰:“诸侯玄衣冕。”《诗经·小雅·采菽》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礼记·玉藻》云:“天子玄端而朝于东门之外”,“诸侯玄端以祭”。 故而,古代服色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传统色彩观。例如,红色的流行,绝不仅仅是色彩本身因素所致,更多的则是传统色彩观所起到的作用。这就是继承汉代以来以黑色、黄色和红色为主的传统色彩观。再具体到唐代而论,红色的流行或是被当成至尊之色,其渊源主要有两点。一是传统色彩观所起到的作用,表明色彩是富有深邃情感的象征世界,不同的色彩有着各自不同的表情,红色的吉祥,黄色的华贵,白色的纯洁,黑色的庄重,等等。色彩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路径之一,它让我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理解各种事物。况且,传统色彩观对色彩的选择和运用又极为讲究,在考虑形色关系上,从“五色”“五行”“吉利”“驱邪”等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规约性意图,不断形成相应的推陈出新的主题。二是西域文化的融入,使得胡化现象日趋明显,服色上表现出多种颜色的碰撞,形成对色彩多样性选择与认定的可能,由此改变了传统色彩观,致使服色变得热烈、奔放。如红色不再是汉代的暗红,初唐至盛唐时变为浓艳明快的大红色。中晚唐时,服色才渐渐以雅致素淡为主,而不再是强烈的撞色。 归纳而言,唐代服色表明这是一个善于用色的朝代,相比服装的形制或服饰的搭配,唐代服色更为后世所称赞。其变化丰富,突出色彩韵律,成为一大亮点。当然,除色彩观发挥作用外,也应归因于隋唐时期染织技术的提高。如现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丝绸实物中,就有唐代的各种织锦,诸如,用染花经丝织成的“广东锦”,用很多小梭子根据花纹着色的边界分块盘织而成的“缀锦”(日本称“缀锦”,我国叫“缂丝”),利用彩色纬丝显花并分段变换纬丝的彩色“纬锦”,以及利用经上显露花纹的“经锦”。“广东锦”的流行(即如今“印经织物”的前身),表明用经丝牵扯成晕色彩条的方法在纺织中的应用(这经丝显花的经锦技术在汉代就已形成);而用纬丝显花,分段变色,可以使织物更加密实,花纹也更加精细,色彩变换更加自由等。另外,“丝绸之路”沿途出土的北朝时期至唐的丝绸织品中,不仅有精致的平纹经锦,还有不少经斜纹绮,如“套环对鸟纹绮”“套环贵字纹绮”,不仅纹饰较汉绮复杂,而且质地更细薄透明。出土的各种五色丝线织成的织锦用色复杂,提花准确,锦面细密,质地趋薄,色泽鲜艳。再有,唐代设有专门的染织生产管理部门,即在朝廷的少府监下,设置有染织署,管理染织作坊,由之提升染织作坊技术等。技术的提升对宫廷服色可谓具有直接的影响。加之民间服色在受到朝廷服色影响的同时,也形成服色相互补充的机制,出现服色来源的多元性。如印染工艺发展到这一时期,蜡染、夹染、绞染等大量民间染色工艺已趋成熟,还兴起了多色染缬,至唐可以说是五彩纷呈,这样的民间染缬工艺也形成对唐代服色审美观的冲击。 “品色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确实是对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强化起到作用,并且波及全社会,甚至影响到全社会色彩观的认同与趋势。《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 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当是时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谓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甚贵,一国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试勿衣紫也。谓左右曰:‘吾甚恶紫之臭。’于是左右适有衣紫而进者,公必曰:‘少却,吾恶紫臭。’”公曰:“诺。”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 这种上行下效,反映了人们的接受心理。再读一读汉代的《城中谣》“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可知,朝廷官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也是形成服色普遍流行的动因,即所谓“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孟子·滕文公上》),上文中提及的唐代女子妆扮的面靥由来也是这个道理。正是这种上行下效的心理,加上对女子服饰从夫从子的要求,唐代女性服色大多都集中在红色、黄色、绿色、蓝色这四大色相上,这与“品色衣”以紫、红、绿、青为主的色彩较为接近。 唐朝“品色衣”制度与自周朝建立的传统冠冕制度,共同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自上古至中古时期的基本服饰规制,对后世影响深远。“品色衣”无疑是唐王朝维护统治、建立更加规范的等级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对于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权力起到了强化作用。唐王朝每一次对“品色衣”制度的修订,真实客观地改变并反映了政治审美心态与宗教影响的波动。尽管有了明确的服饰色彩制度,但也无法阻挡海纳百川的唐朝民间广泛吸纳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各民族服饰风尚。唐代服饰所呈现出的兼容并包且饰绚丽多姿的一面,正说明我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皇室所推崇的服饰色彩也会无意中形成一定的审美导向,由上而下泛化为民间的审美风潮,而民间服饰审美也会自下而上波及皇室审美。就这样,唐王朝在“品色衣”制度规范之下,在外域文明的冲击与本土审美传统延续,以及宗教文明的影响下,呈现出我国古代社会服饰色彩与风尚最为绚烂的一页。 (原文刊发于《艺术探索》年第2期,此处为摘录) 当代名家展厅当代名家展厅 杨卫平油画展 雪塬牧之一 88cm×78cm年 更多文章,扫描治白癜风有什么土方北京有没有专门看白癜风的医院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eiziz.com/qdzz/2122.html
- 上一篇文章: 女神征集令年清水县轩辕文化旅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